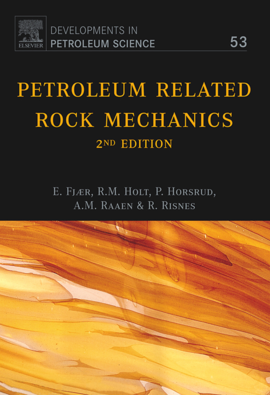李传亮石油观| 意外
0、引言
在对中国石油勘探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后,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意外”。川中会战是“意外”失败的,大庆油田是“意外”发现的……等等。这种“意外”十分普遍,几乎存在于每个油田勘探的每个关节点上。在此意义上,说整个中国油田勘探史就是部“意外”的勘探史,并不为过。
但是,研究界对这些“意外”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在各个油田自己编写的油田发展史和中石油总部编写的总体史( 如《百年石油》) 中,这些“意外”仅仅是作为一个戏剧性的故事记述下来,并没有对其进行专业的科学分析。
我们的研究团队三年来研究了我国十八个油田勘探历史,在此基础上,对各油田普遍存在的“意外”现象进行了归纳分析,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在此呈现给学术同仁,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1、关于研究方法的说明
1.1“意外”的定义与分析框架
所谓“意外”,是指一个事件发生之前的预期与事件的结果明显不一致。因此,一个“意外”事件的发生,首先要具备“事前预期”这个前提。“事前预期”存在于事件发生之前,如果事件的发生与“事前预期”一致,那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只有不符合“事前预期”,才能称之为“意外”。所以,关于“意外”的研究包括三个重要的环节:
(1)“事前预期”是什么? 它是怎么形成的?有什么具体内容? 对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有什么作用?
(2)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任何与人相关的事件,都是与人的控制相关的。“事前预期”决定事件能否发生,并控制着事件的发展过程,这些又决定着事件的结果。
(3)对事件结果的再认识。无论事件的结果是“意料之中”还是“出乎意料”,都要分析其与“事前预期”及“事件过程”的关系,要搞清楚这个结果对“事前预期”意味着什么。
贯穿上述三个环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人的问题。人作为认识与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事前预期”的核心因素,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事前预期”,就会以持不同观点的人之间的争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研究文献中,不同观点间的争论这种“人的冲突”被凸显出来,有时夸张成为一种文学作品式的戏剧冲突。在我们的研究中,只将人作为某种“事前预期”的载体,尽量减少可能导致情绪化效果的“人的冲突”的色彩。
对具体的石油勘探来讲,每一个重大的勘探实践发生之前,小到在哪里布一口探井、目的层设在什么位置,大到是否在一个区域展开大规模勘探会战,在做决策之前总是伴随着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同意在这里布井或会战的人,有其自己的根据,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事前预期”;而坚持在这里布井或会战的人,也有其根据,有另一种“事前预期”。如果坚持者占了上风,井开钻了或会战开始了,事件就发生了,这时反对者已不能控制事件的过程,但他们的“事前预期”仍然存在。事件结果出来后,如果和坚持者的事前预期一致,那么就符合其预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不符合其预期,对坚持者来说就是个“意外”,而对反对者来说则是个“意料之中”的事情。“意外”与“意料之中”必须与某种“事前预期”联系在一起,才有研究的意义。
当然,实际的情况非常复杂,因为很多“事前预期”本身就不明朗,而是模糊的,因此,事件虽然按某种“事前预期”展开了,但结果仍可能出乎其“意料之外”。根据我们目前的研究,中国石油勘探史上的“意外”大多属于这种情况。
1.2 研究“意外”的意义
前文说过,“意外”是我国石油勘探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如此普遍存在的“意外”,让我们开始严重怀疑,与这些“意外”对应的“事前预期”。对石油勘探来说,“事前预期”主要是两部分内容,一是当时的石油地质科学理论,二是勘探者所具有的实际勘探经验。这两个因素决定着他们对井位和油气藏的判断。每次都发生“意外”,每次都促成了他们对“事前预期”的调整。即每次都会对原有的石油地质科学理论有所修正,每次都丰富了他们的勘探经验。这些调整促进了勘探事业的发展,在下次遇到类似问题时,就不会发生多大的争论,也不会再有“意外”发生。但是,如果又遇到了这个新调整后的知识框架内不包含的内容,就又会发生新的“意外”。
对“意外”的研究,实际上就是通过实践来反思科学理论的过程,也是反思我国石油地质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的过程。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了解在我国石油勘探中,理论对实践到底起了怎样的作用,怎样在未来更好地指导勘探实践。
1.3 具体的研究方法
我们选择了国内18个油田作为分析样本(限于篇幅,本文只引用了其中四川盆地、大庆油田、吐哈油田三个样本),逐个还原其勘探史上的“意外”出现的条件与发生过程,深入分析与这些“意外”相关的“事前预期”的内容与来源,并进一步分析当“意外”发生后对事件的再认识,重点在于解释“再认识”的过程对“事前预期”的影响,比如是否有所调整,朝哪个方向调整等。在个案分析基础上,再对全部个案的分析结果进行归纳整理,做各种“类型化”的归纳与分析,以期获得更具整体性的认识。
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我们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充分,有很多技术资料目前没有公开,很多事件的细节缺少更多当事人回忆佐证,特别是关于事后再认识的史料,掺杂进去了很多后人的主观因素,释放出的信息与实际认识情况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基于这种史料条件所做出的研究和判断只是初步性的,有充分的讨论空间。
2、四川盆地的两大“意外”
2.1 “川中”会战的“意外”失败
四川盆地是我国古老的油气产区,战国时期就发现了天然气苗,汉代就有了火井,近代更是出现了磨子井等高产气井,因此当西方的现代石油地质学传入后,四川盆地作为一个油气苗丰富的地区,就成为重点勘探目标。1956年以前,根据山前带找油理论,四川盆地的主要勘探工作都集中在川西坳陷。1955年,康世恩率团前往苏联考察,学习到了地台找油理论。于是,从1956年开始,川中地台也被列入四川盆地的重点勘探区域。此后,地质普查、地震、重、磁、电等物探工作先后在四川盆地展开,人们逐渐对四川盆地的地质情况有了基本的认识。1958年3月,位于“川中”地台的南充构造充3井、龙女寺构造女2井、蓬莱镇构造蓬1井,相继喷出高产工业油流,日产油分别为300多吨、60多吨、100多吨。之后,广安构造、长垣坝构造也相继见到工业油流。于是石油部领导相信“川中”地台能找到大油田,决定在“川中”进行夺油大会战。
1958年4月,“川中”夺油大会战正式开始。石油部迅速从新疆、玉门等地调集人员和物资入川,短短几个月,“川中”就聚集了来自各地的钻井队115个、会战职工36837人。四川石油管理局在“川中”的蓬莱镇、龙女寺、南充、合川、营山、广安、罗渡溪等7个构造上安排了68台钻机,并将南充、蓬莱、龙女3个构造定为主攻目标,在此部署了20口关键井。不料,会战刚刚开始,在所有人都满怀信心准备迎接大油田时,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意外—稳产了2个多月的女2井,在关井测压后居然不出油了。问题出现后,地质工作者研究认为,可能是因为关井后压力发生变化,油运移到了周边,于是便在女2井周围部署了16口“梅花井”。但钻井结果又出乎人们的意料,16口“梅花井”并没有找到油流,而且钻探显示,川中的凉高山组油层储存在致密介壳灰岩和致密石英砂岩中,储层物性属于特低孔、低渗透性,并不容易因压力向周边运移。此外,蓬1井和充3井虽不像女2井那样,油藏突然没有了踪影,但随着井下压力的下降,产量逐渐下降,最后也不出油了。四川石油管理局在3个构造上部署的20口关键井的情况也很不稳定,虽有6口井发生了井喷,但喷油量非常悬殊,最高的日喷油110t,最少的井只捞得8kg油。在这种情况下,地质工作者对“川中”地区油藏性质的认识出现了分歧。绝大多数人仍然坚持“川中”的油藏是砂岩储集层,但以川中矿务局总地质师李德生和南充大队地质师李克勤为代表的一批地质工作者,根据井下取出来的岩心的情况,认为“川中”地区为裂缝性油藏,川中盆地的生油层为侏罗系自流井群黑色湖相页岩,储油层主要是侏罗系凉高山砂岩和大安寨灰岩,这类油层岩石致密、渗透率低,但裂缝发育,油气储存在孔隙、裂缝和溶洞里,其结构十分复杂。因此应该先搞清裂缝的分布规律,进而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但由于当时中国只有延长、玉门、克拉玛依等几个小油田(都是砂岩油气藏),不仅产量低,而且地处偏远,远离急需石油的东部地区,因而迫切希望找到大油田,以增加石油供应、改变石油工业的地区分布格局。因此,四川盆地这一在当时看来最有希望的地区,是不可能被轻易放弃的。虽然问题没有解决,但会战必须继续进行下去。10月26日,石油工业部在克拉玛依召开现场会,会上余秋里宣布进一步加强川中石油会战。李德生等人因为当时特殊的时代环境,遭受了政治上的批判。克拉玛依现场会后,玉门、新疆、青海石油管理局又增派了一批勘探力量。但直到1959年1月,会战仍未取得突破。石油部组织人员讨论后,认为川中地区大面积含油,但地下地质情况复杂,需要收缩力量,下工夫去寻找地质规律和高产、稳产地区。到1959年3月,会战队伍共钻井123口,其中37口井见工业油流,但稳产井仅9口,探明的南充、蓬莱、龙女、合川、罗渡、营山6个油田都不能稳产。因此,“川中”会战总指挥康世恩宣布结束“川中”会战。
“川中”会战结束后,石油部有关领导专家对会战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总结,认为“川中侏罗系油层太致密,岩石孔隙度特别低,出油靠裂缝,3口井喷油是遇上了大裂缝,由于油源接替不上,所以,产量很快下降”。但油是客观存在的,抓住大裂缝还能找到高产区,这就需要有一套对付裂缝性油气藏的特殊工艺技术。在确定了“川中”属于裂缝性油藏后,为了认识“川中”地区裂缝发育的特征和分布规律,四川石油管理局在桂花油田开辟了吉祥实验区,获得了对裂缝的重要认识,似乎找到了女2井的问题的答案。此后,四川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在裂缝性油藏理论的指导下展开,但勘探工作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取得突破,以后的“开气找油”大会战也没有完成预期目标。到目前为止(2015年),女2井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四川盆地的勘探工作。2010年左右,某作业公司在四川盆地打的一口井发生井喷,井喷制服、关井测压后,这口井又不出油了。可见裂缝性油藏的认识,并没有解决四川盆地的地质问题,对四川盆地的地质情况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认识。
“川中”会战后,地质工作者还总结了五条经验教训:一是要选好勘探突破口;二是要搞好新区前期钻探的研究工作;三是对具备基本成油气条件的地区要坚持勘探;四是有目的层但不唯目的层;五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动油气勘探向前发展。余秋里部长也认为石油勘探的基础是:“必须在不断实践中,取得大量的能反映地下真实情况的第一性资料,经过反复试验研究,才能对地质情况、油层性质、油藏类别做出正确的判断”。
2.2 对“川中”会战“意外”失败的分析
“川中”会战之前的预期是这个区域有大的油田,可以展开工程性的勘探会战。之所以形成这种“事前预期”有以下根据。
(1)找油理论中的“上地台说”。这一石油地质学理论深受苏联的影响,当时苏联找油已经突破了早前只在山前盆地找油的限制,在古老地台上,也有重大的勘探突破,发现了罗马什金油田、杜依玛兹油田等世界级大油田,建立了“第二巴库”。学习这一理论,在当时也是紧跟世界前沿、与时俱进的表现。既然苏联能在地台上找到大油田,我们也能。“离山上台”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石油勘探有较大的影响,最成功的例子就是1955—1956年克拉玛依油田的突破。当时,克拉玛依油田地表油气显示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盆地南缘的山前地带(以独山子为中心),一是距独山子以北100多千米的黑油山一带,属盆地地台。关于以何处为勘探重点,在苏联顾问中间就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原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地调处总地质师潘切列耶夫为代表,认为黑油山的油苗是油气向北散逸,油藏已被破坏的“残余油”,黑油山所在的克拉玛依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单斜带,不可能形成大油田;另外一批苏联顾问乌瓦洛夫、尼肯申等则认为黑油山一带有大油藏,即“上台论”,中国的地质专家和决策者接受了这一派的观点,决定在这一区域进行勘探。1955年11月,黑油山1号井钻成出油,1956年9月,这一区域有23口探井喷出工业油流,克拉玛依油田成功发现。克拉玛依的成功经验与“上地台说”是当时石油部决定在川中会战的重要原因。
(2)砂岩油气藏经验。当时,中国只有延长、玉门、克拉玛依三个油田。这三个油田全是砂岩油气藏,当时中国石油科技人员所能获得的实际经验全是砂岩油气藏。根据这种油气藏的递减规律,像龙1、女2、充3井的自喷产量还将持续较长时间,这么高的单井产量在砂岩油气藏区域确实意味着存在一个大的油田。
正是上述两种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构成了“川中”石油会战的“事前预期”,会战的失败意味着这种“事前预期”的错误。
从对事件的再认识来讲,无论是当时,还是直到现在,应该说都没有太积极的正面反馈。以李德生先生为代表的地质科技人员因坚持自己的学术看法,遭到了政治批判,这是当时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后来余秋里也曾向李德生先生道歉。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李德生先生虽然认识到石灰岩储集性能上的特点(洞洞缝缝发育,与砂岩不同),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女2井油藏消失的问题,这种现象直到今天仍时有发生,说明在科学上还是没有认识清楚。而后来总结的那五条“经验教训”,其实也很空洞,缺少实际内容。确切地说,石油地质学并没有从“川中”会战的失败中,获得真正有价值的理论认识。由于这个原因,以后仍有“意外”发生,只不过这个“意外”竟是个“成功”。
2.3 威远气田 的“意外发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前寒武纪是没有大量生命物质的,因此有机论者认为,前寒武纪不具备生成油气藏的条件,从没有人将前寒武纪作为勘探的目的层。因此,威基井在震旦系发现大规模气流的情况,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威基井部署于1956年5月,设计的目的是:“取得四川盆地古生界及元古界含油气资料及基底起伏情况,从而对四川盆地含油气远景进行评估,指出勘探方向”。1958年,钻至2438.6m的中寒武统红椿坪组时,因为钻机超负荷而停钻。20世纪60年代,石油部从罗马尼亚购进两台7000m钻机,其中一台被安排在四川盆地。为了完成威基井的设计任务,1964年3月,四川石油管理局对威基井进行加深。1964年10月,威基井钻至2859.39m震旦系灯影组白云岩地层时发生井漏,现场测试日产天然气14.46×104m3,完井后日产天然气7.80×104m3。从而揭开了威远震旦系白云岩气藏。1965年9月,经过酸化压裂,威远2井日产天然气达到百万立方米。随后,连续打的6口气井,都获得了中高产气流,探明天然气储量达400多亿立方米,证明威远气田是一个高产气田。
威基井在震旦系灯影组地层中发现大气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外。当时,没有一个人认为震旦系会有油气藏,而且威基井的设计目的也绝不是要在震旦系发现油气藏。威远气田发现后,对震旦系气藏的来源问题也相应地展开了研究。到目前为止,关于威远气田震旦系灯影组的气源主要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来自其上的下寒武统,一种看法认为来自其下的陡山沱组和其上的下寒武统,此外,也有人认为震旦系灯影组自生自储的油气也有一定的补充作用。但这些解释的说服力并不强。首先,不能证明下寒武统和震旦系存在生成如此大规模气藏的有机物;其次,按照现有的地质学理论,油气多是“下生上储”,早寒武世生成的气藏是如何实现“上生下储”的?更何况,早寒武世形成的气不仅运移到了其下的震旦系地层,还运移到了其上的中寒武统,“下生上储”和“上生下储”在同一地层同时并存的机制是什么?从威远气田被发现已经50年过去了,至今其气源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
2.4 对威远气田“意外”成功的分析
威远气田“意外”的“事前预期”是这样一种地质学认识:石油是由远古生物沉积形成的,而在寒武纪前并没有出现大量的生命物质(这是当时古生物学的观点,现代生物学认为寒武纪之前很早就有生命存在,只不过还未进化出介壳生物,只是菌藻类的微生物),所以,比寒武纪更古老的震旦纪是不会有油气生成的。但威基井的意外发现,证明这么古老的地层,而且是在灰岩中,确实存在大气田,应该说实践打破了前寒武不能生油的理论认识。
但从事后的认识看,并没有对沉积生油的有机成油论产生怀疑,反而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认为前寒武纪存在的微生物也能生烃。这一认识影响是深远的。当代地球生物学的一个热点就是研究寒武纪前的生物。如果说这种认识有积极作用的话,那就是证明从前寒武纪到第四纪,各个年代地层都可能生油生气,找油不必拘泥于某个年代地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各年代地层都能生油、成藏,虽然突破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常把生油与某一年代地层联系起来的认识,可是却变得更没有依据了。以前还可以凭年代地层去找油,现在年代地层已经没有了勘探指标的意义,找油越来越偏向于找构造。
另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是,无论是“川中”会战,还是威远气田,都是在灰岩中发现的油气藏,可是关于灰岩油气藏的认识并没有在石油系统内得到推广。1975年在华北油田勘探前,出国去伊朗考察回来的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基于伊朗石灰岩油田的经验,提出“猛攻灰岩、大战凸起”的口号,受到普遍的冷落,因为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灰岩中是不可能生油的[9]。但后来任丘的任4井就是在上古生界的白云岩(石灰岩的一种)中发现工业油气藏的,华北油田也由此发现。
在梳理这段历史时,令笔者困惑的是,华北油田的勘探会战是在“川中”会战和威远气田发现后20年左右进行的,也就是说,早在20年前,中国石油界已经在四川发现了灰岩可以生油、成藏,可为什么到了华北勘探时,居然还持那么一种观念呢?作为石油部的高层领导,张文彬等人难道对四川油气勘探的经验一无所知?还要到伊朗考察后才能知道灰岩可以生油?而对张文彬观点持冷遇的其他地质科技人员,难道对四川的经验也一无所知?此中细节,还有待进一步的史料发现才能搞明白,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四川盆地石油勘探史上的两次“意外”,中国石油界的事后认识是远远不足的。
3、“意外”发现的大庆油田
3.1 松辽平原“意外”发现含油气远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东部地区包括松辽盆地并不是油气勘探的重点区域。首先,东北地区发现的油气苗不如西北、西南地区多。其次,当时世界上的主流观点认为,油气是在海相盆地生成的,松辽盆地是陆相盆地,不具备形成大规模油气藏的条件。此外,大小兴安岭一带,广泛分布着各个时期的花岗岩和其他类型的火成岩。再加上日本占领东三省时,在东北地区做了一定的勘探工作,并没有发现工业油气藏。综合以上种种因素,最后得出东北地区找油希望不大的结论。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东北地区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没有人会想到能在松辽盆地发现我国最大的油田。
大庆油田的发现,首先归功于全面铺开的地质调查。从1951年开始,东北地区先后进行了多次油苗调查工作,证实油苗和沥青多处。对松辽盆地的油气勘探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从1955年8月开始,东北地质局派韩景行等人组成踏勘组,对松辽平原进行石油地质踏勘。韩景行等人勘探了从吉林市顺松花江至陶赖昭及长春沿长大线以东及大黑山山脉以西的中新生代地层。对其含油远景进行了肯定评价,认为松辽平原可以找到油气,建议应进一步开展油气普查和物探工作。于是,1956—1957年松辽平原上开展了航空磁测和地面重力概查、电测、钻探等一系列物探工作,初步证明了松辽平原是一个大型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划分了东部隆起带、中部坳陷带、西部斜坡带等构造单元。石油部根据物探资料判断松辽平原是一个含油远景极大的地区,地质部发现了黑龙江省大同镇等13个可能储油构造。
3.2 松基3井 提前试油“意外”发现大庆油田
在发现松辽盆地有含油气远景后,从1958年4月起,石油部与地质部开始对松辽盆地进行大规模勘探。石油部先后在松辽盆地布了3口基准井—松基1井、松基2井、松基3井。松基1井位于黑龙江省安达县任民镇以东14km处(松辽盆地的东北斜坡),1958年7月9日开钻,1958年11月1日完钻,井深1879m,钻遇变质岩,到达盆地基底,钻井过程中没有发现油气显示,完钻后也没有试到油流。松基2井位于吉林省前郭旗登娄库构造的轴部(松辽盆地东南部的隆起区),1958年8月6日开钻,1959年9月15日完钻,井深2887m,在泥浆和岩屑中都见到了油气显示,但试油时没有发现工业油流。
在“川中”会战失败后,松辽盆地的勘探又迟迟不见工业油流,石油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对松基3井井位的设计便慎之又慎。1958年7月,在石油部玉门会议上,松辽石油勘探局就已经提出了在高台子构造上钻松辽盆地的第3口基准井的方案。8月初,地质部提出将松基3井的井位定在吉林省开通县乔家围子正西1500m处。9月3日,石油部和地质部联合开会讨论,最后商定将松基3井的井位定在黑龙江省安达县大同镇高台子电法隆起上,并于9月15日正式上报石油部。10月上旬,松辽石油勘探局的钟其权和长春物探大队的朱大绶等人根据最新的地震资料,把井位做了小幅度的调整,定在了大同镇西北、小西屯以东200m、高台子以西100m处。11月29日,石油部正式批准松基3井井位。
1959年4月11日,松基3井开钻。松基3井设计井深3200m,为了加快钻进速度,从1050m以后才开始取心。原定取心井段411.76m,但由于工具落后、经验不足等原因,只取出岩心202.51m,见到含油气显示层3.15m。取出的油砂呈棕黄色,含油饱满,具有较浓的油气味。在钻进过程中两次从泥浆中反出原油和气泡,现场工作人员将气泡点燃后,火焰呈蓝色,证明是石油气。而且电测资料也表明,井下有较好的油层。
7月下旬,康世恩陪同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钦科和我国石油部苏联专家组到松辽盆地检查工作。在听到松基3井的钻井工程和录井情况后,康世恩要求立即进行电测和井壁取心。两天后,当看到电测资料和从井壁取到的油砂后,米尔钦科等人对康世恩说,要是在苏联得到这样可喜的情况就可以举杯庆贺了。随后,康世恩提出要提前完钻试油,并提出了三条理由。第一,打井的目的就是为了找油,见到了油气显示,就要马上把它弄明白,从这口井的资料看,希望很大,但能不能试出工业油流要看实践。第二,这口井打了1460多米,井斜就有5.7°,井身不直,再打下去钻井速度会受到影响。第三,如果打到预计井深得一年多的时间,油层被泥浆浸泡久了,有油也试不出来,泥浆会把油层枪毙掉……康世恩的提议遭到了米尔钦科的强烈反对,他认为应该按照程序钻至3200m,了解深部的含油气情况,然后由下往上逐层试油。米尔钦科说:“松基3井是基准井,基准井的任务是取全地下资料,这是勘探程序决定的,不能随便更改!”康世恩坚持:“松基3井要马上完钻试油,至于取深部资料的问题,可以安排其他井完成”。之后,康世恩将这一意见上报余秋里,余秋里也同意了康世恩的想法。于是,松基3井于1461.76m处提前完钻试油。
为了圆满完成松基3井的固井、试油工作,石油部组织了一批专家在现场指导工作。8月29日,松基3井的固井工作完成,9月6日第一次射孔,经过20天的反复提捞,9月26日上午松基3井喷出油流,经过正式求产,日产原油13.02t,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2月,在用不同的油嘴、不同的工作制度进行试采后,证实了松基3井稳定可靠,能够长期保持稳产,因此,松基3井成为大庆油田发现的标志。
松基3井的出油,不仅提升了在松辽盆地找油的信心,也给刚刚经受了“川中”会战失败的石油工业带来了希望。不难想象,如果不是松基3井提前完钻,大庆油田的发现还将要向后推迟一段时间,甚至有可能因为没有突破,而中途放弃。余秋里和康世恩都是敏锐、能够灵活变通的领导,在发现有好的油气显示的时候,能够果断放弃原定任务,决定试油,使得松辽盆地能够提前发现工业油流。
当然,石油部能够同意松基3井提前完钻试油,除了康世恩列出的三条原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急需要找到油气来提振所有人的信心。按照当时国际上公认的地质理论以及日本人的勘探经验,松辽盆地的油气勘探前景并不乐观,我国自己的“陆相生油”理论又并未成型,许多人对松辽盆地能否发现大油田是持怀疑态度的。而在松基3井之前的探井虽发现了油砂,但没有一口井发现工业油流,情况最好的南14孔,在钻井时陆续见到含油层20多个,厚达60m,但在试油时也只见到油花,因此松辽盆地的勘探工作面临巨大的压力,急需一个好消息来提升信心,才有了松基3井的提前完钻试油。
3.3 对大庆油田的“意外”的分析
大庆油田的发现也是个意外。松基3井设计深度是3200m,这就是它的“事前预期”,但是什么东西打破了这个“事前预期”呢?事实表明,并非任何石油地质理论,而是两个意外的科技失误因素。一是技术上的小失误,井打斜了,比设计斜了5.7°,再打下去,是什么后果,难以预料;二是地质上的一个小失误,没想到在不到1500m处(即不足设计井深的一半)能发现如此理想的油层,如果事先认识到了,也就不会如此设计这口井了。促使康世恩、余秋里作出提前完钻决策的因素只有两个,一是此前石油部的勘探工作屡受挫折,遭受了“川中”会战失利和松基1井、松基2井落空的打击,石油 行业太需要一点成功来提振士气;二是见好就收的经验主义,松基3井出油后,石油部领导仍不敢据此判断发现大油田,余秋里说“究竟这个油田是大油田还是小油田?是活油田还是死油田?是好油田还是坏油田?还要继续进行更加扎实、深入、细致的工作。”此后又打了多口探井,才决定在大庆展开会战的。说明,当时并没有预想到后来的巨大发现。
米尔钦科是苏联著名的石油专家,其石油地质学造诣与勘探经验都远远超过了“外行”出身的余秋里、康世恩,在作出提前完钻的决定时,余、康两位其实已经置“石油地质科学理论”于不顾了,而后来的实践证明,那些所谓“石油地质科学理论”也根本没有想象中的“科学力”。
关于大庆油田发现经验的认识,是中国石油勘探史上被搞得最为模糊的事件,后来宣传中的“地质力学”“陆相生油说”等事实上与大庆油田的发现并没有关系,因此才有黄汲清等地质学家上书中央领导,要求“讲清楚”之事的发生。关于这个过程,笔者已有专文详细讨论,此处就不复赘述。只是需要强调,由于种种原因,关于大庆油田勘探过程中科学问题的认识,是极不充分的,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4、吐哈油田的两次“意外”
4.1 吐哈油田的“意外”推迟发现
吐哈盆地的勘探工作开始的时间比较早,1892年就开始地质、资源调查工作,1946年开始展开专门的石油地质调查工作,1954年后又展开了地质详查、细测和重磁力普查。之后,吐哈盆地也发现了一些油气显示,但由于台北1井没有试油,大大延迟了吐哈盆地油气勘探的进程。
1958年3月玉门石油管理局进入吐哈盆地开展石油勘探工作,并成立了吐鲁番矿务局。经勘探,发现了36个地质构造和9个潜伏构造,在7个构造上见到油气显示,发现胜金口和七克台两个小油田。1959—1960年,吐鲁番矿务局电法队在原台北重力高上进行电法详查,证实了基岩隆起的存在,地震也发现存在构造显示,分析后认为台北基岩隆起属凹中隆,于是拟定了台北1井井位。台北1井于1960年2月15日开钻,12月24日钻至3122m完钻。在中侏罗统三间房组普遍见油气显示,取心油味甚浓,在岩心面上见黄绿色油珠,油质轻。完井时进行了当时的全套电测系列(当时的电测设备简单,只是自然电位和几条电阻率曲线,也没有气测仪和高精度荧光灯),解释为“水层含残余油,认为此井位于边水附近”。当时参考了玉门的经验,对轻质油缺少认识,因此没有下套管试油,与新油田的发现失之交臂。之后,大庆石油会战开始,吐哈油田的勘探队伍被调往大庆,没有就这一发现继续做工作。1965年后,吐哈盆地的勘探工作基本停顿。
1983年,西北地区石油勘探会议提出了“石油工业勘探重点西移”的战略,吐哈盆地的勘探工作重新展开。1986年,石油部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石油物探局、玉门石油局联合在吐哈盆地设计了一口科学探测井—台参1井。台参1井距台北1井仅1km,台参1井于1987年9月22日开钻,1988年9月2日钻至4466.88m时,在八道湾组煤层卡钻,被迫完井,在侏罗系中发现了油层、差油层近百米,油气显示良好。随后于当年12月至次年2月,对其中5段油层(2934~2972m)进行了试油,在第4层中侏罗统三间房组喷出高产油气流,从而发现了鄯善油田。台参1井喷油后,复查台北1井资料,发现台北1井位于同一含油范围内,其含油层组完全可以对比,由于测井工作不到位,鄯善油田的发现被推迟了近30年。
4.2 对吐哈油田“意外”推迟发现的分析
说吐哈油田被“意外”地推迟发现,其实是现在的说法,当时是个“意内”事件。台北1井的试油环节是可试可不试的。所谓“可试”是抱着“有枣没枣打三竿”的态度,管它有没有根据,把每个流程都走一遍。所谓“可不试”,是指按玉门的经验,这种轻质油显示没有大的价值,没有必要再费工夫试油。这里“玉门经验”就是一种“事前预期”,但事实结果与这种“事前预期”并不一致,这种“意外”打破的乃是“玉门经验”。可是,吐哈经验就有普遍推广的价值吗?当然不是。这种“意外”是司空见惯的,对其反思的后果,就是完善各种作业制度,建立起凡是能取的资料全取,能做的测试全试的烦琐制度。从实践上看,这是一种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疏漏的工程手段,但从科学原理上看,这是理论无能的结果,找不到各种不同地区成油成藏的共同原因,只好以这种覆盖一切地区的全部手段逐一试一遍,其费效比的不合理显而易见。但在没有确切的科学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这又只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此类案例很多,各油田都有,充分说明现有的石油地质科学其实是很不科学的。
4.3 吐哈油田开发结果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
台参1井在侏罗系煤系地层发现工业油流,国内石油地质学家和有机地球化学家们通过研究认为,吐哈盆地的油气资源属于“煤成油”,并根据以往的资源量评估模式做出了资源量评估,但在开发过程中出现了实际结果低于预期目标的情况。
1991年2月吐哈石油会战开始,到1995年会战结束,共钻探井183口、开发井657口,发现柯克亚、丘东等14个油气田和6个工业性含油气构造。吐哈石油会战期间,会战指挥部制定了《吐鲁番—哈密油田“八五”计划》,明确“八五”期间油田要达到如下目标: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3×108t,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200×108m3,原油年产能力420×104t。1992年7月,会战指挥部又提出在“八五”期间,年产量要达到400×104t,争取达到500×104 t。截至1995年底,吐哈盆地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2.08×108t(含凝析油)、天然气储量731×108m3(含溶解气),原油年产量从1991年到1995年分别为20.34×104t、58.58×104t、115.19×104t、141.32×104t、220.82×104t。可以明显看出,除了天然气储量外,石油地质储量和年产量都距预期目标甚远,石油地质储量只达到目标的69.4%,年产量仅达到目标的55.2%。
“九五”期间亦是如此。1996年1月会战指挥部在《吐哈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中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年稳产300×104t,到2000年实现原油年产400×104t,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1×108t,稠油开发实现年产50×104t稳产。实际上,整个油气区的原油年产量只有1997年达到了300.08×104t,其余4年年产量均在(280~300)×104t之间浮动,新增石油地质储只有0.63×108t,虽然每年都会发现新的地质储量,但增速一直在下降。
4.4 对吐哈油田开发结果“意外”的分析
预估吐哈油田储量时,其实依据的是两种“事前预期”。一是传统的砂岩油气藏的经验,前期钻探的数据按以往的经验,就可以落实这么多的储量;二是新的“煤成油”理论,认为煤系为主力生烃层。这两种理论依据叠加在一起,做出当时的储量、产量预期,是合乎“科学原理”的。
当事实结果与预期不符时,人们自然会反省“事前预期”是否出了问题,已有学者提出了煤系地层不能生油的见解,以解释其实际储量远小于预期的原因。在实际工作中,油田的决策者也在反思,几乎每换一届领导班子,都会提出新的勘探方向,提出些新概念,比如页岩油等,但也均未见成效。近期似乎主要以进行体制改革来促进勘探发展。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披露的极少,油田的科技人员和决策者究竟是如何反思这些问题的,尚不得而知,但从试图以体制调整来解决问题的操作手段来看,在科学观念上应该没有突破。
5、总结
在我们所研究的18个油田案例中,在勘探中出现的此类“意外”多达四五十个(还有很多未被揭示,但已存在的),说明“意外”是中国石油勘探史上普遍的现象。翻阅国外史料,情况也是一样。苏联开发“第二巴库”前,力主勘探的古勃金也被讥之为“异想天开”,勘探的结果对这些人来讲,却是出乎意料的。美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探井成功率都极低,大型石油公司的探井成功率为5%,小型石油公司的探井成功率只有1.9%,也就是说失败率高达95%以上,成功都是意外。美国人把探井称作wild cat well,直译过来就叫“野猫井”,就是中文中“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意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石油勘探的不可预期性是多么普遍的现象。
从石油勘探史上存在着如此普遍的“意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石油地质科学理论对勘探结果约束性不强。整个石油地质科学理论是在各国、各地区的勘探实践中不断积累起来的,在积累的过程中,把一些较具普遍性的经验总结为“科学规律”,到今天,其主要内容就是基于有机生油论的“盆控论”“源控论”“断控论”。但这套理论是某个地区局部经验的反映,用到另一个地区就很难成立。可是,勘探工作又总要有个理论基础,那么,这个常常出乎其意料的“理论基础”,事实上对勘探结果是没有约束力的。诚如我们所见,大庆油田成功是出乎“事前预期”,“川中”会战的失败也是出乎“事前预期”的,而这种预期的基础是相同的。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石油地质学的理论了。这个知识体系是怎么形成的?到底有多少真理性?又有怎样的实践价值?该朝哪些方面改进与发展?
(2)通过扩大采集数据的方法,费效比不好。在我国石油勘探实践中,为了降低勘探风险,逐渐发展出一套“大而全”的工作流程,即取全125项资料和数据之类的做法[2],这种做法的思路是将各地的实践经验汇总在一起,在新区全部试一遍,工作量很大,但精确度不高,人力、物力投入较大,导致成本越来越高,不是明智之举。
(3)事后的反思认识不够深刻。首先是反思的态度越来越不好。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勘探目标与“事前预期”不一致时还能激发出热烈的讨论,尽管有时采取了一些不当的行政手段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但讨论问题的状态还是好的,并留下珍贵的科学争论资料。但自20世纪90年代后,针对各油田勘探结果与“预期目标”的不一致,所能见到的公开讨论的资料十分稀少(也许有讨论,但只局限于油田内部,而且非常不彻底)。吐哈油田、冀东油田这种勘探结果出现重大“意外”的案例,几乎见不到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文献。糊里糊涂成功,糊里糊涂失败,几乎成为通例。这非常不利于石油地质科学的发展。
通过对诸多案例的分析,我们得出的总体结论是:现有石油地质科学理论从总体上不具真理性,对勘探实践没有那么大的指导作用(无论是指导其成功,还是指导其失败)。这个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存在,也许正是因为它的作用不大,反正也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也就姑妄言之。在勘探中,实际上各油田各想各的办法。但这个无用的理论体系的存在,妨碍了对实际勘探经验的深入总结,每个实践案例出现的新认识,当上升到理论层面时,要么被这个理论所漠视,要么被其化解于无形,于是“意外”成了常态,而人们对于各种“事前预期”的落空也已麻木,不去想它是怎么回事了。所以,如果想避免“意外”的反复发生,对现有的石油地质科学理论(包括构建科学的基本原则、成烃理论、成藏理论、勘探理论等)进行全方位的反思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