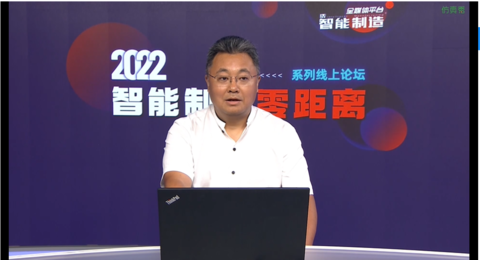关于BIM的几个问题的讨论
前言
近日,在早晨上班的途中,我接到一位建筑行业前辈的电话,希望与我探讨几个关于建筑行业数字化的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也是最前沿、最引人遐思的问题:当下人人都在谈论BIM与AI的结合,那么未来的方向究竟是“BIM+AI”,即在现有BIM技术上嫁接人工智能,还是应该走向一种全新的“AI原生的BIM”甚至“AI原生的BLM(建筑生命周期管理)”?如果答案是后者,那又该如何实现?
第二个问题,建筑行业里常提的“一模到底”,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模”到底指的是什么模?是设计模型、施工模型,还是运维模型?如果各阶段模型需求迥异,又何谈“一模到底”?
电话中,我们共同进行了一场思想的碰撞与梳理。下文,我将尽可能详细地还原并展开我们对这2个问题的探讨过程与思考,希望能为同样身处行业变革浪潮中的同仁们,提供一份参考与镜鉴。
BIM+AI
还是AI原生的BIM或BLM?
第一个问题:BIM+AI,还是AI原生的BIM或BLM?
前辈的第一个问题,直指当前技术融合中最热门也最模糊的地带。他提到,建筑行业里许多人畅想“BIM + DeepSeek”之类的模式,认为只要将强大的人工智能,特别是大语言模型,与现有的BIM软件结合,就能实现智能化。但他凭借多年的工程直觉,总觉得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他敏锐地指出,建筑行业的本质,与制造业一样,是遵循一套严谨的“工艺流程”的。无论是设计建模,还是现场施工,都是一步步、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往下走的。他困惑的是,这个复杂的、充满专业知识的“工艺流程”,究竟该如何与人工智能真正有效地结合起来。
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并告诉他,他的思考已经触及了问题的本质。简单地将一个通用AI“嫁接”到一个BIM软件上,是一种“BIM+AI”的思路,但这条路很可能走不通,或者说,其能达到的天花板会很低。根本原因在于,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BLM)是一个极其复杂、变量极多的庞大系统。通用的大语言模型,尽管在处理文本等单一模态数据时表现惊人,但面对建筑领域高度专业化、多维度、强逻辑约束的复杂问题时,会显得力不从心。你无法指望一个AI在没有深度行业知识和流程拆解的情况下,仅凭“看”就能理解并生成一个完整、合规、可实施的建筑项目。
此外,通用大模型的训练数据主要来自互联网公开 信息,而行业真正的核心知识(Knowledge & Know-how)则源于建筑企业内部的、具有知识产权的数据。企业一般不会把所有这些数据交给通用大模型来训练学习,也就是说通用大模型只能当一个万金油,不堪重用。
我们在讨论BIM+AI和AI原生的BIM乃至BLM时,用了一个有趣的类比。如果把BIM比做是男人,AI则是个美女,BIM+AI,就是男人想找个美女结婚,组建家庭为社会做贡献,但毕竟BIM还是BIM,AI还是AI,不是本质的改变。而两个人生的孩子,同时拥有了BIM的基因,又组合了AI的基因,孩子就是AI原生的BIM。

BIM+AI(协同增强):这指的是BIM技术与AI技术相互配合,AI作为提升BIM能力的重要工具。BIM提供丰富、结构化的建筑数据和环境,AI则提供强大的数据分析、学习预测和自动化能力。这种结合确实像是“组建家庭”,两者各自发挥特长,强强联合,目的是让传统的BIM流程变得更智能、更高效。例如:
AI辅助设计:利用AI算法自动生成或优化建筑布局、管线综合方案,甚至进行合规性检查。
AI赋能运维:通过分析BIM模型叠加物联网实时数据,AI能预测设备故障、优化能源消耗。
AI原生的BIM(深度融合与重塑):这指的是从系统架构设计之初,AI就不是外挂或辅助,而是核心引擎。AI的能力被深度融入BIM的底层逻辑和全流程中。此时的“BIM”可能不再是我们传统认知中的那个软件或模型了,它更像是一个具有学习、推理、优化和自主决策能力的“建筑大脑”或“虚拟孪生体”。这确实有点像“两个人生的孩子”,它继承了父母的核心基因(BIM的数据整合与可视化能力,AI的智能与自动化),但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更具能力的个体。其特征可能包括:
生成式设计(Generative Design):系统能根据目标(如成本、能耗、结构安全)自动生成大量设计方案并自主优化,远超传统参数化设计。
预测性维护与自主优化:建筑不再仅仅是被动管理,数字孪生体能通过AI预测问题,并可能自动调度资源进行维护。
智能语义理解与自动化:AI能深度理解建筑构件的语义信息和设计规范,自动完成繁琐的建模、标注甚至部分决策工作。
对于AI原生的BLM的具体实现,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们要建造一条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这个任务的复杂性远超想象,但我们可以将其分解为一系列逻辑上递进、变量相对可控的步骤。
第一步,是“放线”或“路径规划”。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在广阔的地理空间上,确定一条最优的线路走向。需要考虑的变量虽然多,但却是相对有限和明确的,例如沿线的人口密度、经济据点、地形地貌、地质条件、环保红线、拆 迁成本等等。这些数据很多可以从GIS(地理信息系统)中获取。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训练一个专门的“路径规划AI模态”。这个AI的任务不是设计桥梁或隧道,而是在给定的多重约束条件下,生成一条或多条宏观路径方案。它的输入是结构化的地理和经济数据,输出是线路的几何走向。这个问题的变量是有限的,AI完全可以学习和处理。
第二步,是“关键节点工程决策”。线路走向确定后,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根据具体的地形地貌,决定在何处架桥、何处挖隧道、何处设路基。这又是一个独立的决策过程,可以视为第二个AI模态。这个模态的输入是第一步确定的线路,以及沿线更精细的地质勘探数据、水文资料等。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工程形式的选择,比如“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具体化。这个“决策AI”需要学习大量的工程案例,理解不同地质条件下不同工程方案的经济性、安全性与施工可行性。
第三步,才是具体的“工程单体生成”。当我们决定在某个位置建造一座桥梁后,才进入桥梁本身的设计阶段。这可以被视为第三个AI模态。这个“桥梁生成AI”的输入是确定的桥位、跨度、地质条件以及相关的设计规范。它的任务是根据这些输入,生成一个具体、详细、符合规范的桥梁BIM模型。

通过这样的分解,我们把一个“建造京沪高铁”的、几乎无法直接用AI处理的超级复杂问题,转化为了“路径规划”、“工程决策”、“单体生成”等一系列变量相对收敛、任务边界清晰的子问题。每一个子问题,都可以被看作一个独立的“模态”(Modality)。

这就像下棋。让人工智能学习“下棋”这个通用概念很难,但让它学习并精通“围棋”或“象棋”是完全可行的。因为围棋和象棋的规则是固定的,棋盘是有限的,变量是可控的。我们对建筑生命周期的处理方式,正是借鉴了这种“化繁为简、分而治之”的思想。
因此,真正的答案,不是“BIM+AI”,而是一种“AI原生的BLM”架构。这个架构的底层逻辑是“多模态”的。这里的“多模态”并非简单指文本、图像、声音的混合,而是指建筑生命周期中每一个专业、每一个环节的“专业工作模态”。放线是一种模态,桥梁设计是一种模态,隧道设计是另一种模态,施工进度规划、成本测算、运维管理,都可以被定义为各自独立的模态。
那么,如何实现呢?首先,我们需要为每一个模态,开发专门的、深度学习了该领域知识和数据的AI模型。例如,我们可以用数千个图书馆的设计案例,去训练一个“图书馆生成AI”;用上万个医院病房的案例,去训练一个“病房布局AI”。这些AI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它们处理的是有限变量下的特定问题,因此能够生成高质量、符合专业逻辑的结果。构建AI原生的BLM的方向应是如此,但这要求有提供足够算力的云基础设施和强大的几何、仿真内核,只要有足够、高质量的行业数据集,我们就能为特定的领域(比如桥梁、隧道、住宅、医院)训练出专用的生成式AI。这与国内许多厂商提出的“中药大模型”、“农业大模型”在思路上是异曲同工的,都是在特定领域内,利用有限变量的数据集进行深度训练。这些大模型相对于通用大模型来说,应该算是垂类小模型。
其次,这些独立的“模态AI”并非孤立工作。我们需要一个更高层级的“智能代理”(Agent)来扮演总指挥的角色。这个Agent理解整个建筑生命周期的宏观流程,它知道要完成一个项目,需要依次调用哪些模态AI,以及如何将前一个模态AI的输出,作为后一个模态AI的输入。为了实现这一点,每一个模态AI都必须提供标准的API接口,就像一个个标准化的“算力插件”,可以被Agent灵活调用和编排。
所以,未来的图景是这样的:当用户提出一个需求,比如“在某块土地上,设计一个满足某某要求的三甲医院”,首先被激活的是Agent。Agent会调用“总图规划AI模态”,结合GIS数据和规划指标,生成建筑的布局和轮廓。然后,它会根据规划结果,并行或串行地调用“门诊楼生成AI”、“住院楼生成AI”、“医技楼生成AI”等,生成各个单体的BIM模型。在生成过程中,这些AI会实时交互,例如,住院楼的日照分析结果会反馈给总图规划AI,动态调整楼间距。同时,Agent还会调用“医疗流程仿真AI”,模拟病患、医护、洁污的流线,并将仿真结果反馈给建筑设计AI,进行优化。

在这个体系中,AI不是外挂,而是原生于整个系统架构之中。整个系统是云原生的,支持海量数据的处理和协同;是多模态的,由众多专业的AI模型构成;是由Agent驱动的,能够自动化、智能化地完成复杂的项目任务。这才是“AI原生的BLM”,它从根本上颠覆了“BIM软件+AI插件”的模式,是一种全新的、以数据和智能为核心的下一代建筑行业数字化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讨论的结论是,真正的智能化,不是寄希望于一个无所不能的“通用AI”,而是要回归工程的本质,尊重“工艺流程”,将复杂的系统进行科学地拆解,在每一个环节上,用专注的AI和行业基础数据实现突破,再通过更高维度的智能调度将它们整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合力。
一模到底,一模是什么模?
第二个问题:一模到底,一模是什么模?
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整个建筑生命周期中,设计阶段需要的是设计模型,侧重方案表达和参数化;仿真阶段需要的是分析模型,可能需要对几何进行简化或网格划分;施工阶段需要的是施工模型,要包含深化设计、预制件信息和进度计划;运维阶段需要的又是运维模型,要挂接资产信息和传感器数据。每个阶段的模型用途、精度、信息深度都不同,怎么可能用“一个模型”贯穿到底呢?
谈到全生命周期,我们的第一直觉是将其类比为人的生命。人在幼儿园、上大学、工作、退休等不同阶段,其阅历、经验和使命有着本质不同。但这个人本身,从摇篮到坟墓,是连续、不可分割、动态成长且逐步成熟的。
那么我们需要解释清楚,一模到底的模,也就是模型,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讨论了两个层次的一模到底的模型的理解。
第一个层次的解释,是“主模型+副模型”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一模到底”的“一模”,指的是一个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主模型”(Master Model)。这个主模型是项目的单一数据源(Single Source of Truth),它承载了项目最核心、最稳定、最权威的几何信息和关键属性信息。它是所有后续工作的基础和参照。

而各个阶段所使用的不同模型,如设计模型、仿真模型、施工模型、运维模型,则可以被看作是基于这个主模型衍生出来的“副模型”(Auxiliary Models)或“专业视图”。这些副模型并非凭空创建,而是与主模型有着清晰的、可追溯的继承或引用关系。
例如,进行结构仿真时,工程师会从主模型中提取核心的结构几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网格划分、添加荷载和约束条件,形成一个专门用于计算的“仿真副模型”。这个副模型包含了仿真所需的特定信息,但其几何基础来源于主模型。当主模型中的梁柱尺寸发生变更时,这个变更可以被自动或半自动地传递到仿真副模型中,触发一次新的计算。
同样,在施工阶段,施工单位会基于主模型进行深化设计,添加预制构件的连接节点、钢筋排布、施工段划分、4D进度信息等,形成一个“施工副模型”。这个模型包含了丰富的建造信息,但它依然引用着主模型的设计几何,确保施工是依据最终设计进行的。
到了运维阶段,运维模型会在主模型的基础上,挂接每一个设备资产的台账信息、厂商资料、维修保养记录,并与物联网(IoT)传感器的数据流进行实时关联。
在这个“主模型+副模型”的体系中,“一模到底”的真正含义是“主模型一模到底”。它确保了无论项目进行到哪个阶段,无论衍生出多少专业的副模型,所有工作的核心数据基准都是统一的、唯一的。这解决了传统工作模式中,因数据在不同阶段、不同软件之间反复拷贝、转换而导致的“图模不一致、模模不一致”的根本问题。有些人强调的各阶段模型的差异性,则在“副模型”的层面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体现。主模型保证了“同源”,副模型满足了“专用”。这样一来,看似矛盾的两种观点就完美地统一了。
第二层解释,则更为宏大和彻底。在这种解释下,“一模到底”的“一模”,指的是一个包含了项目全生命周期所有信息的“全模型”(Whole Model)或“总模型”。这个“全模型”不是一个静态的文件,而是一个动态演进、不断丰富的庞大数据库。

这种理念要求我们在项目启动之初,就要有一个全生命周期的顶层设计。在设计阶段,我们创建的不仅仅是一个满足当前设计需求的模型,而是在为一个将要贯穿几十甚至上百年生命周期的“数字资产”打下地基。这意味着,设计阶段的模型,其数据结构就必须预留出未来施工、运维等阶段所需的信息接口。设计模型中就可能要包含一些初步的施工工艺考量、预制构件的划分逻辑、关键设备的运维空间要求等。
随着项目的推进,施工阶段的信息(如实际的施工进度、材料批次、质检记录)、运维阶段的信息(如能耗数据、设备状态、维修工单)会不断地被“添加”到这个“全模型”中,而不是去创建一个个孤立的新模型。这个“全模型”就像一个活的有机体,不断生长,信息不断丰满。
所以,当我们说“全模型一模到底”,我们强调的是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连续性和累积性。设计模型不是被抛弃,而是在后续阶段被不断地“增强”和“扩展”。这种理念,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制造业的PLM(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思想。PLM平台所管理的,正是这样一个包含了产品从需求、设计、仿真、制造、销售、服务到报废所有信息的“全模型”。
全模型的理念,似乎更符合前面举的一个人一生的例子,活的,变化的,逐渐成长成熟的模型。
无论是理解为“主模型一模到底,各阶段副模型不同”,还是理解为“一个不断丰富的全模型一模到底”,其核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建立一个单一、权威、贯穿始终的数据源,实现信息的无损流转和持续增值。这才是“一模到底”的精髓所在。它不是一个僵化的技术指令,要求我们用同一个文件包打天下,而是一种先进的、以数据为中心的工作哲学。
"一模到底"的终极形态是建筑工业的虚拟孪生体,其核心是通过PLM+BIM融合,将传统静态模型升级为覆盖"设计-施工-运维"全链路的动态数据中枢。实现这一目标需在数据架构(参考制造业的MBD/EBOM/MBOM体系)、协同模式(云端实时关联)和政策环境(无图建造法规)三方面同步突破才能真正落地实现。
结语
这场与行业前辈的晨间长谈,从AI与BIM的融合模式,到“一模到底”的哲学思辨,再到具体软件平台理念的演进,虽然话题跳跃,但内核却高度统一。我们探讨的所有问题,最终都指向了建筑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命题:如何从传统的、基于文件的、碎片化的“信息容器”模式,跃升为现代的、基于平台的、一体化的“数据引擎”模式。
“BIM+AI”的简单相加是行不通的,未来必然属于“AI原生”的、基于多模态分解和智能代理协同的BLM系统。
“一模到底”也并非僵化的教条,而是对“单一数据源”和“数据全生命周期连续性”这一核心原则的深刻洞察,可以通过“主模型+副模型”、“全模型”、“活模型”的理念去理解和实现。
这场讨论让我再次深刻地感受到,推动行业进步的,不仅是日新月异的技术本身,更是我们从业者,尤其是像经验丰富的前辈们这样持续不断的学习、追问与深度思考。我最后开了个玩笑,说其实我们人类的大脑就是一种大模型,今天我们的讨论,我们互相塑造了大脑,互相训练了彼此的大模型。
正是这些源于实践的困惑和触及本质的探讨,才能帮助我们拨开繁杂概念的迷雾,看清前行的真正方向。尽管建筑行业的工业化与智能化转型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未来可期。而这一切的起点,或许就始于这样一个个坦诚、深入、回归常识与本质的切磋。